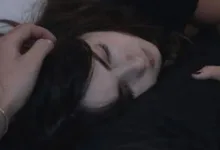有时,看见那些想要找主或奴的贴文令我费解。因为在我自己,一段关系或对象并非借由「寻找」来,而是经过「培养」才能成就。

对于找到对象,我是没有值得一提的意见的。先求有再求好当然是一种方式,不过相较于想找位主人/奴隶,我偏好的看法应该是找到喜欢、合适的对象,再让他做自己的主人/奴隶。若非如此,这段关系的根基其实相当脆弱。
因为我们声称自己爱着对方,实际上只是对方身处的位置或身份,而非占有这个身份的「人」,于是,我们将对方给「物化」了。
物化本身最大的问题在于,一段关系里的彼此双方并非是以真诚的自我进行投入,而是排除与筛选掉了部分的自我与他人产生联系。
自然,主奴本是个体的部分呈现,在相处上强调这点并无不妥,可当我们只注意对方的身份时,我们同时也忽略掉他/她的人性面。
换句话说,这更倾向于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。我悲观地认为,此类关系在彼此将对方过多视为「身份」或「工具」时,就几乎注定了它的破灭。毕竟,这意味着只是对方在这个「位置」,可这个「对方」并不具有无可取代的价值。
好比,我们会在一段关系里互相称爱,事实却可能是我们只将彼此视为填补自身的工具;于是在某些偶发事件产生时,那个工具的「效用」跟着失去,被填补的缺口随之显现,而关系因此生变。
不过,要自己在面对他人时无所求实在困难,但在更具功利意义的关系中,总有那么一个瞬间,你会发现联系着彼此的,那原以为很「有爱」的桥梁,实际竟是这样脆弱乃至于经不起几次动摇;而自己在意识到对方某一缺陷时,也没自己所预料地这么爱惜对方。
那些能经历风雨而依旧维系着感情的双方,除去对双方的身份认同,还包含对身份拥有者的个人认同。这样的个人认同才是摆脱物化利用的开端,也是使感情再深化的关键,才能真正触到文章开端言及的「培养」。它让关系在受损时还能由其他联系所支撑,不至于立刻土崩瓦解。
论到培养,或者称其为双向调教也不为过。可这类的状态是双方的适应,没有主导与被主导的阶级意识,是明白关系两端的个体都有其独特性,并愿意去进入对方的主体意识,以及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对与理解自己。这种过程不只在主奴关系前,也会在关系进行中持续。
若是双方都仅将对方视作「身份」,同时皆以「物」的态度去应对,除了体验以外是难以获得自我成长的,还会在其中感到一种匮乏。因为,任何一种「工具」都有耗损的可能,而在被我们所调用的部分之外,其实并没有什么了。
于是容易感到虚无,并将意识到彼此从没真正接触到对方。他们在匮乏里注意到内在有某块角落无法被对方填补,与其说自己爱对方或被对方所爱,更多是感到自己需要或被对方所被需要。
工具之间无法互相滋养,双方只在意到对方能否符合自己的「需要」,在这样彼此耗损的过程里,终将因一方无法满足于另一方的期待,便直接导向了结束。
若要建立深厚的连结,则必然得要在自己的需要之外,还得超越自身的需要以关注他人,要晓得他的独特性,并帮助对方在关系里以自己的方式成长。对人的耐性以及自身对旁人的爱意会产生好奇,使得自己更愿意跳脱自我来帮助关系里的另一半,促使关系里的双方在更深入彼此灵魂之际,还加深了关系的羁绊,让对方的存在不只流于「身份」,而是被你肯定、接纳的「个人」。
如此,双方的爱意才算真正建立,而在互相关注的过程中,你会意识到自我在情感上变得丰富,而不是变得匮乏。你内在的需要不是非得将对方当作填补的工具,不必这样才能抚慰自己,只要有个人存在着某种天性,愿意在关系里与你的理解日渐加深,他愿意去注意你的存在、关心你的成长;在关系之外,他还想成全你的自身,并不是为了你所能提供给他的某种价值。你们用同一种天性去贴近彼此,这时你会发现,原来你们这才真正相遇过。
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。试着想了一下,倘使面对了真诚地与我产生联系的对象,我会这么说:
「我说爱你,不是因为我的爱无处堆放,不是因为你正好在我眼前,而是因着你是你自己,让我在想照顾你之余,还想让你阅览更多风景,想跟你分享我所见过的世界。
我也好奇你的感觉,想知道这个世界在你那里有什么不同。想知道你有什么样的需要,心底深处埋藏着什么秘密,过去走过怎样使你不幸与幸运的路,又是为何我们走到了一起。
我想看见你的成长,即便你的成长可能意味着你对我依赖的消退,加深了我们分别的可能,但我相信你会做出当下所理解的最好判断,无论如何,我依然会为妳的成长感到安慰与骄傲。
如果我们失去彼此,世界依然会沿着本有的轨道继续运转,我们都有各自的将来,谁也不会一蹶不振。而我们都晓得,双方没有谁非谁不可,可我想,若是你也在的话就更好了。」
待人怀以热诚与信任,用真诚的自我去碰真诚的对方,在关系之外也愿意看见彼此。
用最大的爱意去理解,在尊重对方的前提下,将他带进自己的生命,并接受他与你不同的选择,让彼此都有资格拥抱与放手,不滞不溺不沉沦不执著,随顺自然。
我们都在学习的过程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