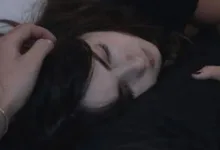许多人在亲密关系中,常常感觉自己像个“奴隶”——不断围着对方转,满足对方的需求,身心俱疲却难以停下。这种消耗,让不少人对亲密关系望而却步。

而另一些人,则在关系中扮演“主人”的角色,享受支配一切的权力感。可一旦对方表现出反抗,他们便容易陷入崩溃与不安,甚至开始怀疑:自己曾经拥有的“控制”,是否从来就不曾稳固?
无论是恋爱还是亲子关系,我们目睹了太多关系陷入“支配—屈服”的结构性困境中,痛苦纠缠,难以脱身。
事实上,只有建立起一种“互为主体”的关系,亲密才能真正深入,幸福也才成为可能。
那么,为什么我们那么容易掉进“支配-服从”的模式?这种关系背后,隐藏着怎样的深层心理逻辑?它的结局往往是什么?我们又该如何走向成熟、健康的亲密关系?
这篇文章将带你深入亲密关系的相处本质,其中或许会有令你震撼的瞬间,甚至可能颠覆你过往对“亲密”的认知——值得静下心来,细细品味。
“支配-屈服”关系模式
我们深陷于“支配-服从”的关系而痛苦,根源往往并非“爱得不够”,而是我们尚未学会如何与一个“真实的他者”共存。
我们或许精于扮演“功能性角色”,也习惯了与“功能性的人”互动:有人负责养家,有人负责顾家,有人负责成才。然而,当面对一个有血有肉、有情感需求的真实个体时,许多人却感到无措。
真正亲密的联结,渴望的从来不是“我被需要”或“我被顺从”,而是——我的感受能被你看见,我的存在能被你理解;同时,你也是一个我由衷尊重、不愿吞噬的独立灵魂。这是一种深刻的彼此承认:我们都将对方视作独立自主的主体。
唯有当我敢于承认:你不是我想象中的延伸或附属,而你也能看见:我不是你实现目标的工具,我们的关系才能真正走向真实、深刻与自由。
遗憾的是,这种“你是你,我是我,而我们彼此承认”的结构常常十分脆弱。一旦它出现裂痕,我们便会不自觉地退行至两种防御姿态:要么成为“主人”,通过控制、忽视或情感勒索来确认自我的存在;要么沦为“奴隶”,通过讨好、牺牲与依赖来换取对方对自己存在的肯定。这已非两个完整灵魂的相爱,而是一种心理上的“主奴结构”——在支配与屈服中,彼此消耗,彼此囚禁。
为什么“彼此承认”如此艰难
一个真实的“自我”,唯有在另一个独立主体的“承认”中才能诞生。然而,这份承认必须来自一个我们也认可的、同样独立的主体,才具有意义。这意味着,如果你不将对方视作一个完整的人,那么他对你的认可,也将失去力量。
可现实中,一个人常常无法、或不愿把对方当作独立主体;又或者对方自己也丧失了“做自己主人”的勇气,难以被当作一个真正的人来对待。
我们可以从婴儿与主要抚养者(如母亲)的关系中,理解“自我”是如何在承认中建立,又何以崩塌为“支配-屈服”的结构:
在早期的母婴互动中,“我承认你,你也承认我”不仅是情感的纽带,更是自我意识的根基。婴儿通过母亲的回应——微笑、抚摸、注视——体验到“我是有能力的”。母亲并非婴儿幻想的延伸,而是一个活生生的、自主的“他者”。在这样的互动中,婴儿感受到:“我影响了她,她也影响了我”。自我正是在这样的张力中逐渐浮现。
然而,这种“相互承认”极难维系,因为它内含一个根本的矛盾:我想确认我的独立,却必须依赖你来确认我的独立。
这个悖论在婴儿心中引发强烈的不安:若要独立,就必须放弃对母亲的完全控制,承认她不是自己可随意支配的对象;但那份“我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存在”的感觉,又离不开母亲的关注与回应。
如果母亲无法适度回应——例如过度侵入或过度撤退——婴儿在独立与依赖之间的张力便无法调和,自我的建构受阻,形成深层的心理冲突。
当母亲过度侵入(如过度保护或控制),婴儿会感到自我被吞噬,无法确认自己是独立的主体;
当母亲过度撤退(如冷漠或忽视),婴儿则因缺乏回应,难以确认自我存在的真实性;
而当母亲仅将自己视为满足孩子的“工具”,她也很难将婴儿视为完整的“人”。婴儿于是学会:妈妈不是人,我也不是——我们只是彼此使用的工具。
这样的心理状态容易陷入循环:渴望独立,却感到被控制;渴望回应,却感到被忽视。张力无法平衡,相互承认随之崩塌,关系便滑向支配与屈从,健康的自我再难建立。
从婴儿时期起,我们就深深渴望“被看见”。如果这个需求早期未能得到充分回应,长大后的我们,便会用极端的方式去索求:
控制:无法忍受被忽视,通过支配他人来确认自己的存在
屈从:害怕被抛弃,以全面服从换取对方的关注,避免惩罚
情绪化:担心需求不被回应,用激烈情绪呐喊“快看见我”
冷漠:害怕需要会受伤,用疏离掩盖内心的脆弱。
支配与服从,从来不是简单的权力游戏,而是自我与他者之间无法承受的张力。我们在关系中痛苦,往往不是爱得不够,而是害怕被否定、害怕失去自我。
我们恐惧在他者眼中不再是独立的主体,而沦为附属或工具,于是陷入支配与屈从的恶性循环。就像生活中那些被困在角色里的人:“全能妈妈”、“乖孩子”、“只会挣钱的爸爸”、“老好人”……他们无声地诉说着:
“我什么都为你做,只求你别走。”
“我失去自己,才能换来你的存在。”
“我忍受你的控制,是怕你不再爱我。”
他们以屈从换取存在感,以牺牲维系关系。以为那是爱,却可能早已远离了真实相遇的可能。
施受虐:相互承认的扭曲替代
在性的领域中,施受虐关系将“支配-屈服”的动态演绎到了极致,也揭示了这种关系的深刻逻辑与其必然的结局。
杰西卡·本杰明在《爱的束缚》第二章中分析了著名小说《O的故事》:女主角O被男友带至“罗西城堡”,沦为彻底的性奴。她被迫服从一切命令,丧失身体与意志的主权。然而她的每一次屈从,却仿佛都在追寻某种更深层的联结与意义。后来,她被“转赠”给男友的兄长——一位更为冷酷、理性、无情的“主人”。O对这位主人的服从甚至发展到愿为其牺牲生命的程度。
支配的本质,不在于身体的占有,而在于对他者意志的驯服。在这类关系中,真正的权力并非体现于肉体控制,而在于心理上的完全征服:支配者的快感,来自于他者必须屈从,并通过这份屈从来确认自身的存在。而受虐者的“快感”,亦非源于疼痛本身,而是来自一种“我被注视、我被连接”的强烈体验。
对受虐者而言,受虐行为具有三重心理意义
1. 通过疼痛获得确认:身体的受创等同于“我存在于你的意志之中”。我在施加的感知中,获得了自己“真实存在”的回应。
2. 在屈服中成为主人的一部分:“我不再是我自己,但我可以在你之中继续存活”。通过彻底的屈从,个体虽失去自我,却在主人的意志中寻得了某种替代性的存在感。
3. 逃避被抛弃的恐惧:“只要我服从,就不会被丢弃”。屈从成为抵御终极孤独与被弃命运的惟一途径。
这三点共同揭示了支配关系中的共谋性——奴隶通过屈从参与了自身的被压迫,并从中换取某种扭曲的生存意义,同时也更深地陷入控制的循环。
然而,这种关系的最终结局并非高潮,而是死亡。当一方彻底屈从,另一方的“存在感”也将随之消散。一旦双方停止挣扎,欲望的张力便告瓦解,关系走向寂灭。
支配者无法再从奴隶身上获得“真实的承认”,因为奴隶已被彻底物化,沦为工具。
奴隶则因失去自我,陷入虚无与抑郁,在心理上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主体,其存在完全依赖于主人的界定与回应。
最终,双方共同坠入一种孤独、空虚、死寂的状态。这种主体承认的枯竭,标志着亲密关系的彻底崩溃。
成熟的亲密:两个主体的冒险
杰西卡·本杰明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——“相互承认”。这不仅是她理论体系的基石,更是理解亲密关系中爱与欲望如何流动的关键。
什么是相互承认?
它意味着:我视你为一个拥有自身欲望、边界与思想的完整的人;你也看见我,不是你的幻想投射,而是一个真实、复杂且独立的存在。
然而,实现这种承认极为不易。它要求双方既能活出自身的主体性,又能看见并尊重对方的主体性。这必然伴随着两个内心世界与人格结构的真实相遇,甚至激烈碰撞。
具体而言,它至少需要我们同时做到:
1. 自我主张
我能说出“我是谁”,而不仅仅是“我是你的谁”。我敢于表达自己的需求、受与期望,不再将自己禁锢于他人的期待或要求之下。
2. 承认他者
我接纳“你可以与我不同,甚至可以拒绝我”。我们彼此承认对方是独立的主体—你不是为我而存在的完美幻象,你有权不同意、有权拒绝,甚至有权在某些时刻离开。
3. 承担冲突
当差异与对立浮现,真正的考验来临。我能做到不试图控制你,也不逃避你,而是与你共同面对我们之间的分歧,在张力中寻求真实的连接。
亲密关系真正的力量,并非源于控制,而是来自于相互影响。唯有当我们将彼此视为独立而完整的主体时,这种影响才能真实发生——我们不再是彼此实现欲望的工具,而是能够真正触动和改变对方的生命。
在这样的关系中,社会所赋予的角色(如妻子、丈夫、孩子)将不再成为主轴。取而代之的,是每个个体鲜活而真实的自我,成为联结中最珍贵的部分。
成熟的亲密关系,从来不是依附、控制或屈从。它是两个独立的主体,在相互的承认与映照中,共同展开的一场冒险与成长。
当我们真正学会“相互承认”,我们便从“彼此控制”的困局中走出,迈向“彼此影响”的广阔天地。由此,我们得以超越角色的束缚,进入真正自由的相遇与生命的交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