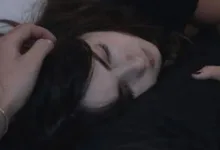有部分女粉私信我,集中反馈了被性骚扰产生癖好的困惑。她们几乎都有一个高度统一的现象,就是每天都期待私信99+,甚至更期待这些骚扰式的私信可以硬化,以至于产生了这种现代化的小众癖好。为了这点老陈醋,我特意包了这顿饺子。

对于部分女性产生社交媒体被性骚扰皮的情况,首先最重要的原因在于,那些本应令人厌恶的提起骚扰,有时却在特定语境下被部分女性转化成一种确认自我存在的手段。她当然不是因为她们喜欢被羞辱,而是因为羞辱本身激发了我依然有性吸引力的快感。这种感受来得隐秘而迅忙,既不光明又不完全黑暗。尤其是在情感关系匮乏、自我认同感低下时,任何一个被欲望指向的信号,都可能产生强烈回应。越是匿名,越是粗暴,越是越界,就越能制造我值得被追逐的强度感。
弗洛伊德在自然论中提到,一个人对自身的自恋越是不稳定,就越需要他人的欲望来加以确认。当这种确认以骚扰形式出现时,他虽然令人不适,但也确实缓解了情绪,击打了迟钝的自我。更隐秘的是,性羞耻一旦与兴奋回路绑定,就容易形成导错机制。越被污名化的感受,越容易激发竞技魅力。而越禁忌的事情,越像在跨越一道红线时留下体温,这不是谁故意迎合,而是羞耻感激活的兴奋路径越平淡,对话更强烈,越被看见的证明。
如果童年时期,个体长期处在不被尊重、不被保护的环境中,比如遭遇老师羞辱、家庭中年长男性侵犯,那这些未被言说且未被修复的经历并不会真正结束。成年后,当个体在社交平台中接收到一些冒犯性的靠近时,例如被挑衅、被凝视,身体就先一步识别出熟悉的气氛、情绪并非来自骚扰内容本身,而是源自于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反应的惊艳感。愤怒、反对、拉黑发朋友圈、控诉,这一整套流程并不陌生,而恰恰意味熟悉形成了某种掌控感,即童年时的上一次只能沉默,这一次可以回击!
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写道,人不断重复那些创伤是为了掌控它,但这种重复里藏着趋利本身的快感。也就是说,即便这种重复令人不适,他也能唤起久违的情绪强度。羞辱、惊吓、愤怒与被看见的错乱混合,会打破日常的迟钝,使人重新感知我还活着。
个体可能并不主动追求骚扰,但身体记忆却将这种越界误认为唯一能激活兴奋的来源。欲望并不总是源于温柔,也可能生长在羞辱的土壤里。部分个体的情绪机制中存在一种错位的自由性,当工具与欲望混合出现时,大脑反而更容易点燃兴奋。这并不是表层的迎合,而是一种更深层的结构。受虐与施虐需求在身体内部混合存在,一句充满侵犯意味的私信既打击了尊严,又激活了渴望,反而形成了其欲的高潮感。
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提到,压抑欲望的力量注定会寻找到其他形式的释放途径,而语言骚扰往往就是这种释放的通道。他粗暴、直接,没有情感包裹,却恰恰精准的击中了一种你值得被欲望的幻想。
而更深处还有一个难以被察觉的机制,潜隐的自毁冲动,那些从小被忽视、否定、边缘化的个体,很可能已经悄悄在心底建立起一个信念,“我本就不配被尊重”。所以,每一次冒犯,每一次恶意的凝视,不仅没有打碎自我,反而像是对这个信念的确认。
有时,骚扰并不终结于关闭死血,而对一些个体而言,真正的快感不在于被骚扰的当下,而在于对骚扰者的反控着,一种冷淡、不理、轻蔑的姿态成为了情绪的武器。“你越贱,我越不理你”。这种看似被动的回应,实则是一种精密的操控策略,“不是我无法回应你,而是我选择不回应你”。
齐泽克在实在界的鬼脸中写道,“享乐的真正位置,往往藏在禁止与否定之中”。也就是说,个体一边骂着别再来,一边却在刷新私信页面,等待下一条刺激性的出现。在这套机制中,骚扰者的执着反而成了一种情绪攻击。“每一条令人作呕的私信都像是一个情绪提款机,被静默提取,再用冷漠击碎,个体借此完成一次自我修复,不是因为我有魅力,而是因为我能操控你,哪怕你是最低级的方式靠近我,都能让你碰壁”。这是羞辱的逆转,是一种代偿性的复仇。最后分享一句话,结束今天的思考。“最猛烈的拒绝,常常来自最深的渴望”。